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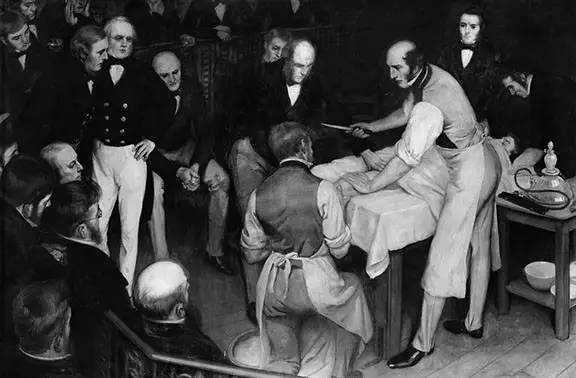
不只是数字(节选)
文 | [美]彼得•于贝尔
译 | [美] 张琼懿
我告诉患者豪尔赫·埃尔南德斯(Jorge Hernandez),这次开给他的药对血压和心脏都有好处。他点头一副非常认同的模样。但是他接着脸上表情一沉,充满担心地问我:“有副作用吗?”我解释说几乎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有很少数人刚开始服用时会出现头晕,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咳嗽,不过只要一停药这些症状就消失了。“那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吗?”我告诉他,几乎所有的药物都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但是就这个药物来讲,产生副作用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什么样的副作用呢?”他继续问道,“比如什么?”
我有一种要虚脱的感觉,相信很多临床医生也遇过这种情形。我已经尽我所能让这位患者了解各种治疗选项,也跟他说明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并且尽量不去提那些极为罕见的状况,以免吓到他。不过,我显然要破例了。我用非常冷静的语气告诉他:“在非常少数的状况下,使用者可能会出现肾脏问题。”
“很严重吗?”
“大概就是在血液检查时出现轻微异常,可是停药后几乎都会恢复正常。”
“只是几乎?”
我们又继续聊了一会儿,但是结果已经很明显,他一定不愿意吃这种药。
患者赋权运动因为有了决策分析这项利器相挺而更上一层楼,这个新领域使用了一种名叫决策树的方法,它以患者的个人偏好为中心,将各种医疗后果的发生概率和患者效果同时进行比较,以便让患者在面临难以抉择的医疗决定时可以做出最适当的选择。这些决策树展现出极具逻辑的决策过程,每一个步骤都很有条理。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状况下,发生概率小的医疗后果理当不如一个发生概率高的医疗后果更重要。
然而,这位患者却执着于几乎不会发生的事而不肯罢休。我在入行的早期曾在某个医疗机构担任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目的是确保参与试验者明白所有和这项研究有关的风险与益处。因为有这样的委员会,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那些无辜的智障孩童,就不会再被利用来进行肝炎病毒或癌细胞的实验。也因为有医疗试验委员会,医生必须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不管发生概率再怎么低的风险,都清楚告知参与试验者。我在人体试验委员会的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委员非常认真地执行这项新规范,他们严格要求,不管有多琐碎、发生的概率有多低,进行试验的医疗人员都必须详尽地告知参与研究者该研究的所有风险,唯有如此才允许患者参与研究。
但是不管是人体试验委员的经验,还是和埃尔南德斯这种患者的对话,都让我对这个新规范有了一些省思。我知道患者有被告知的权利,如此一来,他们才能评估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各项治疗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我并不认为将所有的风险都告诉患者是帮助他们做出理性判断的明智之举。我不知道应该向患者透露多少信息,会不会在我提到一些发生概率极低的副作用之后,他们反而对原本应该是最有利的选择避之犹恐不及呢?
有一天,我又为了同样的事情感到头痛不已,于是,我决定用一个假设的情形做个实验。我以在医院餐厅享用午餐的、身体健康没问题的人为调查对象,请他们想象一下,如果他们被诊断出患了大肠癌,然后有两种可能治愈疾病的手术可供选择。
为了让你更了解这个实验,请你也做同样想象。这两种治疗方式如下:
第一种是没有并发症的手术,它的治愈率有80%。但是有20%的概率无法除去所有肿瘤,导致你最后因为这个癌症死去。
第二种是有并发症的手术,它的治愈率比第一种高,但是有可能出现几种罕见的并发症。和第一种手术一样,在没有任何并发症的情形下,它的治愈率可以达到80%,但是你会因为这个癌症死亡的概率只有16%。那么,剩下的4%呢?它们分别是第一个1%,你会被治愈,但是必须一辈子使用肠造口袋;第二个1%,你会被治愈,但是你会有长期腹泻的情况,平均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得起床跑厕所;第三个1%,你会被治愈,但是手术伤口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愈合;第四个1%,你会被治愈,但是肚子上的伤痕时不时就会疼一下。
我必须先澄清一下,这两种手术是我捏造出来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我只是利用它们来评估大家做选择的方式,特别是看看后面提及那一连串发生概率很低的并发症会不会把患者吓跑,让他们因此放弃其实比较有利的选择。这些并发症听起来虽然有点可怕,但是严重程度绝对比不上死亡。所以,患者实际面对的其实是“并发症与死亡之间的选择”。
当我要求这些人在结肠造口或其他并发症和死亡之间做选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选了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再怎么糟,也好过一命呜呼。
这么说,大家选择手术治疗方式时,应该都会为了多出来的那4%存活率,选择可能产生并发症的第二种手术方式。没想到,结果并非如此,大部分的人竟然都选了不会有并发症的第一种手术方式。我们之间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做结肠造口或死于大肠癌,你会选择哪一个?”
“做结肠造口。”
“腹泻或死于大肠癌呢?”
“腹泻。”
“伤口感染或死于大肠癌呢?”
“伤口感染。”
没有人选择死亡,因为“这些情况都好过死亡”。
“好的,那么第一种手术和第二种手术,你选择哪一个呢?”
“第一种,没有并发症的那一种。”
这样的反应让我很纳闷,我问道:“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那些并发症再怎么样也好过因为大肠癌死亡吗?”
“是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选第二种手术,总觉得怪怪的。”
这个简单的实验清楚点出这种新世代医疗模式下的隐忧。很多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算把做医疗决定时应该要知道的事项都告诉患者,患者还是有可能做出不合理的决定。例如患者已经说过宁愿做结肠造口也不愿意因大肠癌而死去,最后竟然矛盾地选择不会出现结肠造口,但死亡率较高的治疗方式。这中间显然有某种不理性的冲动,让患者放弃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大部分的医生都知道,医疗决定并不是单纯的医疗事件。我们已经从律师、伦理学家、决策分析师那得知,医疗决定的正确与否与患者的个人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不是每个医生都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光是良好的沟通能力并不足以让患者做出最好的决定。以这个大肠癌实验为例,患者其实很清楚我所提供的信息,他们自己也说了:结肠造口好过死亡,腹泻好过死亡,伤口感染好过死亡。然而,他们却无法选择最好的决定。
正确做决定不只是了解事实的问题,了解了也不见得可以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有时,做决定凭的是感觉,而不是思考。当患者听到与风险有关的信息,比如副作用发生的概率时,真正影响他们的不是这些副作用的严重性,而是心理上的感受。
数字无理
确实有很多理由,让医生对患者是否真的了解这些“统计资料”抱有怀疑态度,只要看看前面几章所提到的沟通误会就不难得知,患者对医生的解释常常听了却没有懂。以下面这段录音内容为例,对话中血液专科医师正在跟患者解释白血病治疗的优缺点,他希望患者可以考虑接受化疗:
“如果我们看的是慢性期的完全细胞基因反应率,效果大概有80%,如果是增生期,效果大概是15%。所以说,这种药对进程中的病情效果并不好。如果我们来看基克利的化疗试验结果(IRIS),反应最好的状况,也就是那些出现完全细胞基因反应率的患者,他们在接下来四年,也就是四十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病情加重的概率大概是8%。”
“听起来还不错。”这位患者回答。
“嗯,现在我们来看费城染色体呈阳性但属于慢性的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会变成增生型或者急性芽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有完全细胞基因反应率,也就是那些在试验期第六个月出现完全系基因缓解的患者,就和你一样,概率可能低于5%,所以……”
“四年吗?”
“是的,”医生回答他,“看一下这边的曲线图。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稳定减缓的情形。变成增生型的概率大概是每年2%—4%。”
“可以请您再说一次吗?”患者忍不住插话道,“我听不太懂。”
这位患者当然听不懂医生在说什么。在这段不到两分钟的谈话里,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数字,一下子是80%、15%,既是四年,又是四十八个月的,任谁听了都会头昏脑涨。而这段对话的实际长度其实超过一个钟头,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患者还会被告知,就算他进入完全缓解期,接下来的四年,他的癌症还是有5%的机会会变成增生型,另外,有4%的机会(医生并没有清楚提到多久时间内)会出现染色体上的改变。如果有复发情形,他可以考虑做骨髓移植(这个议题又引出了另一段五到十分钟的对话,内容讨论了骨髓移植的存活率,以及宿主对移植物产生排斥的概率:“发生概率大概在40%—50%,如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概率会提高到70%左右”),之后出现慢性复发的概率大概是5%—8%,但是,这得看……够了吧,我有必要继续讲下去吗?
医生是一群对数字很精明的人,自然会把事情数字化。因此,和患者谈话时经常不知不觉搬出一堆数字,而且会把比例(例如3%)和发生概率(每一百个就有三个)互换着说。3%不也就是一百个中有三个吗?是的,但是很多患者就是这样被搞混的。当记者请纽约扬基队的传奇捕手约吉·贝拉(Yogi Berra)解释棒球的错综复杂时,他回了一句让人满头雾水的名言:“棒球有90%是心理战,另外一半靠技术。”
很多民众其实无法理解这些基本数学运算。美国达特茅茨学院(Dartmounth)里两位研究风险沟通的医生史蒂文·沃洛辛(Steven Woloshin)和莉萨·施瓦茨(Lisa Schwartz)做过一项调查,他们问一般民众:“如果你拿一个硬币丢一千次,大概会出现几次人头呢?”结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错误。掌握决定权的患者做出对自己不利或者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懂数学。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用数学,况且,患者做抉择时遇到的数学挑战也不仅仅是百分比与频率间的转换。以我稍早提到的大肠癌的例子来看,大部分人都想避开并发症,宁愿选择病死。我对这个现象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不管是数学好或不好的人,都做了同样选择。我再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美国各地的医生,发现也有差不多一半的医生选择了没有并发症的第一种手术治疗。
请相信我,这些医生对这多出来的4%存活率绝对有充分的了解,他们也一定知道死去与做结肠造口的差别,我实在无法相信他们竟然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忍受腹泻或暂时的伤口感染。所以说,理解与选择之间是有一定落差的,就算是非常有数学头脑的人,做决定时还是无法避免受到数字感受的干扰。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伦·彼得斯(Ellen Peters)做过一个试验,她在两个罐子里装入彩色软糖,其中一个罐子标示9%的彩色软糖是红色(里面放了一百颗彩色软糖,其中有九颗是红色),另一个罐子上标示10%的彩色软糖是红色的(里面放了十颗彩色软糖,其中有一颗是红色)。接着,她请参与试验者从罐子里摸出一颗彩色软糖,只要摸出的彩色软糖是红色,就有奖金。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直截了当,10%的概率显然高过9%,但是很多人却僵持在罐子上写的一颗与九颗上。大家都知道应该选择标有10%的那个罐子,但是九颗听起来就是感觉比一颗多。
当然,数学能力愈差的人愈容易选择标有9%那个罐子,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单纯是理解问题,还牵扯到情绪问题,就算他们知道正确的答案,却依然对自己没有信心,导致对那个红色糖果比较多的罐子更加难以抗拒。医生只要不断丢出数字就足以让患者的心情变糟,失去做决定时该有的判断力。
看清真相
医疗选择与我们在一般生活中遇到的选择很不一样。我每年都会到百货公司添购衣服两次,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便可以挑到符合我的颜色、材质以及价钱要求的衬衫。偶尔,我也会买到那种穿几次就坏了的衣服,但是我一点也不讶异,因为我挑的几乎都是大甩卖的商品。反正,万一缩水不能穿,就给我儿子捡。几年下来,我对买衬衫已经很有经验,很少买到不合适的衣服,就算偶尔买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上百货公司挑衣服和做医疗决定显然不同,买衣服的赌注小,不太牵扯到情绪,也没有过于复杂的数字需要理解,更是人生习以为常的经验,就算做错决定,后果也是短暂的,再说,补救方法多得很。但是,要在保留溃烂不治的脚与截肢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刚得知自己患癌症后,必须立刻选择开刀治疗或放疗,就不是这么容易了。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医疗决定好像也并非那么不同寻常。我是深受修车师傅同情的人,每次他提到我那部十多年的本田雅阁又有毛病时,我就像是一位在和医生对话的患者。因为我不懂车,所以只好寻求修车师傅的建议。医疗决定也有点像购房贷款,让人摸不着头绪的统计数字多得是,例如现在的浮动利率是4%,接下来的三年内有50%的可能性会上升2%以上,到时候,我得缴的房贷就会变成……
面对这些情形复杂而且其中利弊关系让人混淆不清的决定时,大家自然而然会把焦点放在最重要的信息上。然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信息呢?假设你为了做近视激光治疗,上网搜索眼科医师的数据,最后锁定两位候选人。
其中一位医生是哈佛医学院毕业,他使用去年才购入的新一代准分子激光。他在网站上声称他已用这个方法进行八十多次手术,结果非常好。
另一位是艾奥瓦大学毕业的医生,他使用的也是同一种激光,并且有三百多次成功的经验。
这时候你会选哪一位医生呢?当我和我的同事布莱恩·齐克蒙德-费舍尔(Brian Zikmund-Fisher)用这个假设性问题进行试验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来自艾奥瓦的医生,因为他的经验丰富,使用的技术也先进。(不过,在我去做演讲的学校中,有一所学校的学生一边倒选择了另一位医生,不用我说是哪一所学校了吧?)但是,如果我只提供一位医生的数据,有些人得到的是哈佛医生的数据,有些人得到的是艾奥瓦医生的数据时,哈佛医生获选的概率就高多了。
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大家对于哈佛医生的八十次经验究竟是多还是少无从比较。因此我们只知道这位医生并不是新手,不知道八十次称不称得上是经验丰富,而哈佛大学学历确实为他镀了一层金。但是在艾奥瓦医生出现后,我们便会觉得哈佛医生的经验并没有让人感到特别惊艳。
患者面临重大的医疗决定时,往往缺少比较各种治疗方法时所需的全盘信息。像是五年内患癌症的概率为3%就很难让人体会。我们很少会去想象自己在某个特定时段内,发生某种不幸的概率是多少。所以,在患者赋权的医患模式下,患者会从医生那里得到许多数据,然后急欲将这些资料纳入自己的考虑中,在做决定时也深受这些数字影响。这么做有好有坏,例如,有了足够数据,便可以判断一个医生的经验是否足够,但是,另一方面,患者也可能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数字影响,例如他人的风险概率。
患者赋权必须付出代价,患者可能会被各种治疗方法搞得一头雾水,接收了一堆数据,却又缺乏评估它们的能力。数字会影响情绪,而情绪会改变人对风险概率的感觉。
情绪在做决定时扮演的角色
著名爱尔兰作家、诗人兼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过:“情感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我们误入歧途。”确实,人生如果没有偶尔被情感冲昏头的时刻,比如与明知道最后会甩掉自己的女孩子交往、在疯狂派对上牺牲色相等等,该有多乏味呢?王尔德为感情冠上带有讽刺意味的冠冕,意思是只要能够驾驭情绪,理性就可以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本章似乎再次给了情感不好的名声,但这并不是重点。情感并非总是引我们误入歧途,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得凭着情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
有些人因为受伤或生病而失去情感,却依然保有理智,但他们却经常做出不可理喻的决定。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在名著《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达马西奥以大脑额叶受伤的患者做一系列重要实验,这些人依旧保有高度认知能力,可以有条理地分析所做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往往不合逻辑。他们知道哪个选择是对的,但无法同时用感觉体会那是对的选择,因而无法和自己的推理同步。情感的诞生说到底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经常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劲儿,最后也证实这些事情真的不对劲儿。
很难说做决定时有情感介入是好是坏。有时候情感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但是也经常出现直觉反而正确的情形。不管是好是坏,情感经常在做选择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只不过十分微妙,让它经常被忽略。
这种对情感的忽略才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由新医患模式架构起来的世界是将情感排除在外的。生物伦理学家和律师所急于雄辩的都是个人权利、患者自主权等,他们认为患者只要了解全盘信息,就能依个人价值观,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199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患者自决法案》,要求各医疗机构必须善尽患者预先医疗指示的责任,好在患者病情严重到无法做决定时,医疗机关可以事前便知道患者的意愿。除此之外,政府也督促医疗研究中心成立人体试验委员会,其重要职责之一是详细审阅提供给患者的同意书,以确保患者可以完全了解其内容。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强制要求制药公司必须在药品标示上列出所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这些新措施都以理性作为基础,再次强调完整的医疗信息与患者自主权是患者做出医疗决定的磐石。
大家不断在这些道德、法律等重要议题中打转,对于情感可以说只字不提。大家急于把医疗信息提供给患者,却忽略了这些信息可能带给患者的感受。
医生与患者一路跌跌撞撞走到共同决定这个新纪元,有些医生想让患者尽可能了解自己的医疗选择,到头来所用的医疗术语却让患者愈听愈茫然,医生则完全没察觉患者的情绪需求。患者也有类似的无知,虽然没听懂医生的话却自以为听懂了。另外他们也自认够了解做结肠造口的感受。最重要的是,他们丝毫不知自己的理性其实受到了心理因素的深刻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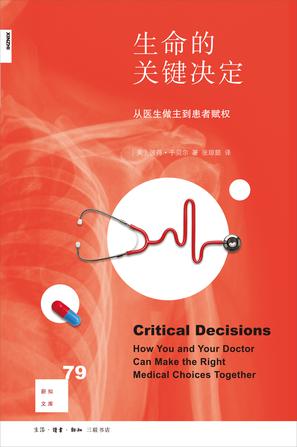
作者: [美]彼得·于贝尔
译者: 张琼懿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6
ISBN: 9787108058775

地址:中国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 电话:8610-64001122
Copyright © 2013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权所有 | 技术支持:云章科技
ICP备 案 号:京ICP备120112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