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人类学特有并日益传播至其他领域的写作文体,民族志正在跨越学科,走向大众;它的特点、主题、产生方式和行文技巧要求写作者兼顾专业与通俗,明晰与优雅。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学学者如何书写民族志,才能承载不同阅读者对之的要求与期待?
5月10日,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雅理联合主办“云端新读书”第7期于线上展开,几位参与者共同阅读三联书店新书《人类学写作工具箱》(克里斯汀·戈德西著),讨论民族志的诸多性质,并延及对学术写作的反思,对专业写作行动的省察,以及人类学老一辈写作者的故事,以期新一代写作者能够薪火不绝,把人类学对生活充满智慧的洞察传递下去。本篇内容为活动的文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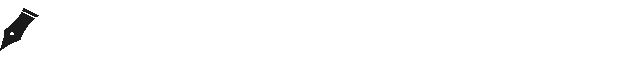
理论之上,生活之下
人类学写作的手与心
整理者 | 张芮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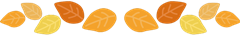
张芮宁(主持人)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对刚进入人类学的年轻学者极具助益,本书作者克里斯汀·戈德西是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她将自己关于田野笔记和民族志的写作经验凝聚于此,该书于202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因实用且轻快的行文风格一经出版就广受热议。
人类学是一门需进入隐秘,方可获得整体的学科,它以研究者浸泡在经验中的做法,来感受外部世界在普通人心灵结构中的存在形态,以此呈现出人的独特性。而民族志,用书中的话所说,是人类学为人类生活的差异性创造的一个安全世界。因此,民族志需增进人们对混杂世界的理解,让研究者对经验现象的见解得到被研究对象的理解,也需以朴实、生动的叙事风格得到不同学科的认可,拔高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这就需要民族志的写作呈现出清晰化的风格,对此戈德西根据自身二十年的亲身经历,对青年学者如何写出一本可读性强的民族志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
当读者拿到一部优秀的民族志时,往往看不见这部作品创造的后台,为此作者在本书中将这个后台一步步为我们呈现出来,她用自身及诸多学者民族志写作的生活史为我们提炼了人类学写作的十二法则。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
[美]克里斯汀·戈德西 著 卞思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2月
ISBN:9787108077431
首先系主题的选择,作者认为研究主题往往会和原创性、田野地点的选择、介入的身份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影响到研究者在民族志研究时所做的决定。戈德西尤为看重原创性,一方面在穷尽前人研究的情况下,能测试研究者对该主题的兴趣程度,另一方面这也是研究者建立自身学术权威的努力。
其次系田野笔记的写作,戈德西认为详细而有活力的田野笔记为详细而有活力的民族志提供了基础,对人类学来讲,往往在田野中没法预先得知主题,因此需要大量翔实的记录,在这个过程中初学者需要避免“无意识的总结和评论性措辞”,注意收集行为细节的描述并用一些行为细节的描述来代替那些形容词或副词,与此同时需详细记录田野报道人的话,以便在后续民族志的写作中将其转变为文学性的对话。另一方面涉及到地点的描述需要收集地图,拍摄大量的照片,这使研究者对一个地方的空间布局有了大致的原始材料,也为后续民族志写作增添了地方的生动性。
再次系民族志的写作,作者强调在民族志的写作过程中,将一个有情感的自我融入到材料中有助于保障其资料的真实性,并将田野笔记中的线索串联起来。而在田野笔记的整理过程中,民族志可以描述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关系、该地的历史、地方与居住者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时间、空间、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紧接着便是整合理论,民族志与田野笔记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理论回应,戈德西认为理论决定了研究者带到田野里的问题,但决不允许理论渗透到田野笔记当中去,相反强调参与观察,利用自己的经验质疑或颠覆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当研究人员将所需理论编织到民族志的文本中,就可以开始对文章进行不断调整,这种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民族志的可读性,例如减少复杂的科学术语以及使用尾注来提高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注意力,再比如减少被动语态的使用,通过使用主动语态,将完整的信息呈现出来。同时,对主句而言,主谓之间不能相较太远。这些修改是一个不断重复、不断循序递进的过程。
最后,关于写作,作者认为写作是一种随着时间和实践发展的技能,写好文章不存在神奇的方法,也不应该等到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才开始写作。因为民族志的写作是建立在不断的审查—修改—完善过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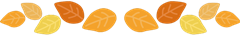
卞思梅(主讲人)
田野中的人是最活络的人
本书的翻译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书的原名为From Notes to Narrative: Writing Ethnographies that Everyone Can Read,强调了从笔记到叙述的转变,这是人类学写作的核心过程。从笔记到叙述的转变,实际上象征着人类学写作的空间转变。进入田野进行田野笔记写作,是一种关于远方的空间与经验的体现。叙述,即将笔记转换成为一种写作文体,将之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民族志的空间想象就是人类学谈及的“从田野回到书桌前”,而书桌其实是对一种感受的象征,一种进出的将笔记消化的过程。

Kristen Ghodsee, From Notes to Narrative, 2016
01 清晰化写作
戈德西强调写作的本质在于交流,一方面写作是为说服别人,另一方面是在说服别人的同时将自己的观点清楚地表达出来。而在写作中,作者往往陷入意识流,当事人也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此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发出明确的指令,别人才能够接收到。写作的清晰化需要进行一个阶段性区分,学术写作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是清楚自己写作的目的,其二明确自身所处位置。博士论文与出版书的清晰化程度不同,就前者而言,受众主要是针对博士论文的评委,博士论文是进入学术的入场券,在深入浅出把握文字之前需先弄清复杂的理论,因此博士论文写作就需要使用一些本学科的专业词汇,并且接受这个学科的专业训练。对后者来讲就不同,这里戈德西也讲到在美国很多学者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而这些书籍的受众与博士论文的受众存在区别。
02 主题选择
人类学的研究主题非常重要,一旦进入到田野,这个主题会伴随研究者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人类学的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主题的选择将会改变研究者的整个精神状态,比如说某位人类学家去研究珠宝,后来他成为了珠宝商,又或者他去研究别的东西,人生履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研究主题;90%的研究者选择研究的国家后,都会被他所研究的国家的文化影响。
戈德西谈及原创性,认为可以选择一些未被涉入的主题,也可以用一些新的视角去阐释已有的主题。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在这个过程中去令自己兴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找到一个喜欢的东西,越了解就越能走进去,变成一个喜欢的主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在家附近还是去国外调查的问题,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都能创造出优秀的民族志作品,不过关键在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体验。局内人就是研究自身所处的环境,若他进入田野后发现和原来记忆中的印象不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人类学的观点去透视。作为局内人去研究自身文化,是一个将熟悉化为陌生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读大量的民族志,形成一种对文化的敏锐性,包括观察力、敏感度。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虽是局内人,但要形成一个局外人的目光,然后用局外人的目光去打量熟悉的地方。对于局外人来讲,就是要化陌生为熟悉。
03 将自己融入材料
随着人类学文化理论的更新,它逐渐强调反身性写作,把自我带入到写作中,让读者知道研究者是怎么发现这些事情的或者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对此民族志的典型写法就是从一个场景描述开始,比如我今天去哪,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然后这个思考随之而放大成为我的整个研究主题。通过一个小事情开始,带入自我的视角,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材料里面。这种写作一方面会增强读者的代入感,另一方面提高材料的可信度。
04 加入民族志细节
民族志细节关乎田野笔记的记录,当研究者刚进入田野时都是比较亢奋的,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看到很多能记的东西,可这个“蜜月期”一过就发现田野笔记越写越简单,按照戈德西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一些“无意识的总结与评论性的措辞”,尽量做大量的行为细节描述。我有一些在田野中收集资料的技巧,例如问当地人母亲、奶奶等长辈都是从哪些地方嫁到这儿来的,接着去画家谱,画完了以后,整个社会结构就基本上把握了。再接下来去画地图,尽量让当地人来画,这样就会发现每个人画的结构一样,但实际的表现不一样。在这些地图里面就会发现他们的空间想象不太一样,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笔记,最后回来写的时候会发现非常有用。也可以运用摄影,拍摄照片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纯粹记录。当研究者回到“书桌”撰写民族志时就会通过照片唤醒对当时这段经验的记忆。当这些细节唤醒研究者的记忆以后,民族志才能够写得比较精彩,才能够去写出细节。我建议青年学者从事田野工作,需要提高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就像小说里面一样去生动的描述。
05 描述地点和事件
戈德西之所以强调对地点和事件的描述,在于唤醒地方的历史。在收集这些关于地点与事件的细节时,一定要多听少插嘴,这有助于迅速提升对该地整体情况的了解。因此,人类学学者需要是敏感的人,养成对细节的关注,接着从细节反过去看人,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训练自己。
06 整合你的理论
事实上戈德西非常反对用现有理论去统辖材料,这意味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受理论影响预设了很多东西,导致进入田野所看到的现象都是理论想让研究者看到的。当研究者打破这些预设,并发现理论无法框住这些材料的时候,这就是他寻求理论突破的时刻。因此,当青年学者遇到什么细节,觉得不对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感觉。因为这说明该细节可能跟既有的一些概念、理论是有冲突的,这个冲突点可能就是你的突破点。
这就是扎根理论的思路,民族志中的理论是在研究者填写的材料里呈现的。当这些材料很散漫的时候通过对它的组织就会攻破那些理论预设。由此民族志的写作需要大家更多地进入田野。一旦进入田野后发现很多生套的东西就会打破我们静态的理论思维。田野里的人很活,例如观察汉藏之间的羌族丧葬仪式,会发现他们信仰佛教的轮回,又有带有独特的羌族信仰,认为死了以后会回到祖先的地方。它们矛盾却又并存着,因为田野中的人是活络的人。
07 民族志的修改
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时,我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小组——系博士生们建立的非正式讨论小组,这个小组每学期都会有人负责组织并两周举行一次聚会,聚会过程中大家进行头脑风暴,批评彼此的文本。如果你希望有师友对你的论文提出修改建议,可以联系负责人并提供相应文本,这样的讨论会使文本愈发完善。而在具体的论文修改中可以先修改文章结构,后修改词句,在对文章精美化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播放软件将它念出来,听听自己的文章。最后,“找到自己的过程”,对此需要调整环境,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习惯,在习惯之上不断创作,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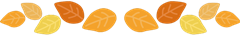
尹韬(与谈人)
平衡文思,赓续学脉
这本书是人类学写作方面的重要参考之一,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指导如何写出清晰、引人入胜且具有公共性色彩的民族志。同时,人类学写作不仅是人类学家的基本技能,也是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
尽管中国人类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写作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学术断裂,以及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前辈的努力,可以看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情况。这一历史导致了当前中国人类学理论思考或田野观察,较为忽视勾连理论和田野的写作这一关键环节,特别是如何在宏大的题目和具体的分析之间找到平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前学术作品中存在大量的“空泛”现象,即题目宏大但内容空洞,学术写作具有公共性,学术作品应该能够与公众沟通,而不仅仅是学术圈内的交流。如果考虑到历史学家田余庆的作品因其深入浅出而受到广泛阅读,我们会知道《人类学写作工具箱》的推出非常及时,它不仅对人类学学者,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写作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这本书提供了一种从收集田野材料到完成民族志的实用写作框架,有助于学者提高写作质量。
中国人类学曾经拥有写作的传统,如林耀华的民族志小说、费孝通的人类学散文、田汝康的诗意民族志、于式玉的旅行通讯等,这些传统在当代人类学写作中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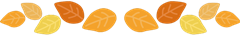
劳佳琦(与谈人)
理论只是舟筏,生活之树长青
这本书非常实用,作者手把手教导我们如何撰写清晰有趣的学术研究。同时,书籍的趣味性使得阅读体验流畅且引人入胜。虽然这本书名为《人类学写作工具箱》,但其意义不仅限于人类学,对所有学科的学术写作都具有指导和警醒意义。任何学科的学者都需要具备写出清晰、吸引人的文本能力。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的学术表达,这涉及到学术写作的审美。目前法学界有对晦涩难懂的学术作品的偏好,我自己也有因写作风格被质疑的经历。我呼吁学术界应该鼓励清晰、有吸引力的文本表达,而不是晦涩难懂的学术黑话。
目前盛行晦涩的学术写作风格对学生带来了一种不好的示范作用,并对他们产生了规训效果,导致学生不自觉地在学术表达上变得僵化。我在教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学生难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观点,导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同时,年轻学者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主题,因为当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对主题的热爱可以帮助学者坚持下去。追随内心热爱的研究可能与主流热点不符,进而在课题申请、学术发表方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都是自我选择应该承担的代价。食得咸鱼抵得渴,凡事都是有得有失。学者只应该有出色和平庸之分,而不是主流和边缘之分。一时的热闹不重要,时间终会证明谁在金线之上。
至于在田野调查中如何处理材料和理论的关系,我想所有的理论只是尚未被否定的东西。理论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基础,但不能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限制。理论源自于生活,理论不能去框定生活。学者在田野中应该学会超越理论框架,以观察和理解生活本身。理论只是舟筏,是指月的手指,生活本身才是目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
最后,年轻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因此学者应该允许自己有写出糟糕初稿的自由,并通过不断的修改和改进,最终形成优秀的学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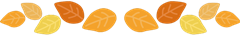
苏诗毅(与谈人)
写作的责任与写作者的未来
首先,我代表北京三联书店感谢参与活动的各位老师和观众。这本书是三联与雅理合作出版的一本非常实用的轻学术作品,收入三联“雅理译丛”;出版方请了受过最好的学术训练的译者,来译介国外知名学者受关注的轻学术作品,以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书里没有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完全以作者戈德西教授的个人写作经验和心得为主,她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知行合一地实现了书里主张的观点。
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书中提供了从心到手的全方位、各层次的写作技巧,以及一份长长的民族志杰作书单;其次,结合了丰富的名家名作、案例分析,使得内容可读有趣;最后,书籍的装帧也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体验,采用了小开本和空脊锁线的可爱设计。
人类学对自身专业写作行为的自觉反思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点,民族志写作范式在马林诺夫斯基、《写文化》那里的革新对学科发展有着别具一格的重要性。人类学关心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涉及文本正当性问题,因为人类学是一种主体对他者的观察、描述和再现,作者对立场、视角、评价等的选择必然会影响民族志的面貌和性质;而被书写的对象有权利要求被书写得如其所是,这是人类学写作不能逃避的责任,否则就会产生一种话语或知识的暴力。人类学学科需要持续关切写作本身、持续思考这个伦理问题。
书出版后,我们收集了一些读者对书的反馈,其中包括“书更加适合美国的学术环境和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者”的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近年来,国内对非虚构作品的关注度在上升,我想,专业学者可以,也应该通过优秀的写作积极影响大众和社会,我在此想表达一个对国内人类学学者的期待,希望我们的学者也能够基于中国视角和汉语特点,推出一本适合中国读者的“人类学写作工具箱”,以培养我们下一代的民族志书写者,把学术和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写作和文字连接起来,把人类学对生活充满智慧的洞察分享给更多的人。

地址:中国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 电话:8610-64001122
Copyright © 2013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权所有 | 技术支持:云章科技
ICP备 案 号:京ICP备120112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