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对《艺术哲学》一书的重视屡屡溢于言表。他不仅在《译者序》中肯定了丹纳的实证主义,盛赞其丰富的史料,而且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手抄该书第四编《希腊的雕塑》,遥寄英伦,作为提高傅聪艺术修养的读本。其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一再提及此事,以证傅雷的爱子之心,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也说明了傅雷对《艺术哲学》的偏爱。
* 文章节选自《傅雷的美术世界》一书,吕作用 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内文有删节,详尽注释请参考原书。

傅雷(一九六一年)
“以科学精神改造中国学术” 
在世人眼中,傅雷首先是位著名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三十余种作品,约五百万字,其中大多为法国小说,尤以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为主,但也不乏美术译著,包括丹纳的《艺术哲学》、葛赛尔的《罗丹艺术论》和牛顿的《英国绘画》。在此三种艺术译著中,数《艺术哲学》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艺术哲学》是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的著作。丹纳自1864年起在巴黎美术学校讲授美术史,《艺术哲学》一书系当时的讲稿,自1865年至1869年分编陆续出版。在傅雷留法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书是一本较为重要的美术史著作。我们今天常见的《艺术哲学》中译本,是傅雷于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而傅雷第一次翻译此书,还是在他留学法国的时候。
傅雷初译《艺术哲学》是在1929年,但当时只译出第一编第一章。根据《傅雷年谱》“一九二九年”条下载:“九月二十日返回巴黎后,即投入休养中开始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一篇第一章,于十月十一日译毕,并撰写《译者弁言》。”这里的《艺术论》就是指《艺术哲学》第一编第一章,在《华胥社文艺论集》发表时名之以《艺术论》。
傅雷之所以翻译《艺术论》,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在译完《艺术论》后的1929年10月底,傅雷撰写了一篇《译者弁言》,附于译文前一起发表。在《译者弁言》中,他阐明了翻译该书的原因:
“然而我之介绍此书,正着眼在其缺点上面,因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尤其是艺术常识极端贫乏的中国学术界,如果要对于艺术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非从这种实证主义的根本着手不可。”
提出以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改造中国学术,对一个21岁的青年而言当然是难能可贵的,有论者称颂他“在东西文化交融的大文化背景下,保持着清晰的头脑,思索着艺术理论和艺术现象,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弊端与不足,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初入艺术领域便充分展示出他的过人的艺术敏锐力和独立思辨力……”这固然没错,但也应看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启蒙的成果已广泽人心,科学精神至少已为新派知识分子所接纳并视为救国良方,因此傅雷有这样的思想似乎也是必然的。
当然,对21岁的傅雷而言,“以科学精神改造中国学术”固然是翻译此书原因中“公”的一面,那么,他的另外的原因——即“私”的一面——便是提高自己的法文水平。傅雷在1947年12月答《大公报》问时提到最初的翻译动机,他说:“我第一部译的书,是梅里美的《嘉尔曼》,同时还有《高龙巴》,都全部译完(一九二九年),因系求学时代的练习,译后即丢得不知去向。”1957年在《自述》中再次提到翻译之初衷:
“20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绝未想到正式翻译,故稿子如何丢的亦不记忆。回国后于1931年即译贝多芬传。以后自知没有能力从事创作,方逐渐转到翻译的路上。”
既然翻译《嘉尔曼》和《高龙巴》都仅仅是为了“学法文”“作学习文字的训练”,那么同年翻译的《艺术论》便可认为也有同样的目的。
特殊时期的忘我投入 
然而,《艺术论》只译出第一编第一章,无论于“公”于“私”都不是傅雷的初衷。《译者弁言》的最后一句,傅雷写道:“译述方面的错误,希望有人能指正我。译名不统一的地方,当于将来全部完竣后重行校订。”可见傅雷原意是要译出全书的,但《艺术论》发表后,傅雷的译著不断面世,唯独此书迟迟未见续译。直到1958年,傅雷才开始重译《艺术哲学》。
《傅雷年谱》“一九五八年”条下:“六月至翌年五月 翻译丹纳《艺术哲学》,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一〇四幅……”此话虽然简单,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次翻译对傅雷而言不仅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中进行的,而且翻译及出版过程也花费了傅雷的不少心血。
从1957年8月开始,上海作协针对傅雷召开了十多次批判会,傅雷作了多次的检讨,最后还是在次年的4月30日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次变故对傅雷的打击是深重的,朱梅馥在1958年4月19日致傅聪的家书中有一段关于这段时间傅雷的身体情况的描述:
“爸爸的身体很糟,除一般衰弱及失眠外,眼睛又出了毛病,初发觉时常常发花,发酸,淌泪水,头痛,他以为眼镜不对,二个月以前请眼科医生验光,才发觉不是眼镜之故,根本是眼睛本身的病,因为用脑力视力过度,影响了视神经衰退,医生说,必须休养三四个月,绝对不能看书,用脑,要营养好,否则发展下去就有失明的危险……爸爸的头痛,吴医生断为三叉神经痛,一天要痛二三次,厉害的时候痛得整夜十几小时连续不断,非常苦恼。牙齿也去检查过,拔掉过几个,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休养了两个多月,眼睛仍无多大进步,因此我心里也烦得很……”
就是在这样身心俱伤的情况下,傅雷着手翻译《艺术哲学》。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傅雷正是经历了政治上的打击,才潜入书斋,翻译出了《艺术哲学》《搅水女人》《比哀兰德》等作品的。这种观点不仅符合时间顺序,在逻辑上讲也合情合理。不过,傅雷决定翻译《艺术哲学》,在时间上要早于他遭批判的1958年8月,而恰恰是在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的1956年。傅雷在1959年2月26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提到:“至五六年春任叔、效洵二先生来沪时所约定的丹纳《艺术哲学》,初稿已完成,现在校改第二道,第二道以后尚须校改第三道,预计五月中可以誊出。”在现存的傅雷书简中,有32通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函,其中不少涉及《艺术哲学》一书的翻译、编辑和出版问题。在这些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翻译《艺术哲学》的艰辛。1959年5月底,经三道校改的《艺术哲学》译稿寄出,傅雷在5月29日致出版社的信中写道:“兹另邮挂号寄上拙译丹纳《艺术哲学》稿一部,计目录二十四页,译序五页,正文四一〇页,人名表十四页,版权页用西文一页,共四五四页,请检收审阅。”
字里行间,我们大抵已看出傅雷一丝不苟的态度。但傅雷对《艺术哲学》的校改工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他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校改的机会。比如他在1961年1月12日致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近无意中翻阅所存译文底稿,发现尚有文字细节需略加润色,若蒙寄下再改一遍,尤为感荷。”这次修改大抵是在校样中完成的。1961年4月2日开始,傅雷对《艺术哲学》的三校样进行校阅。他在1961年4月9日致儿媳妇弥拉的家书中提到“这两星期,我在校阅丹纳《艺术哲学》的译稿”。他的校阅也极其认真细致,“该稿全文虽由本人校改二遍,并由家人通读一遍,漏校处仍恐难免。”上文述及,在初稿完成后已校改三道,而在校样过程中又校改二遍,这样《艺术哲学》的翻译校改达五遍之多。而这一切,仅仅是傅雷为《艺术哲学》的出版所作的一部分工作而已。
傅雷为《艺术哲学》译本所作另一项重大工作是有关插图问题。丹纳的法文原版并没有插图,傅雷认为那是因为“国情不同,他们名作流传甚广,群众对美术馆中重要作品类多熟识”,但在我国则必须加入插图,否则“颇有纸上谈兵之憾,对读者无益”。在加入插图的意见获得出版社同意后,又专门致信,详细陈述有关插图问题,包括:(一)本书性质与插图的关系,出版本书的主旨;(二)本书的开本、插图用纸及装订、制版的技术要求;(三)插图的选择及多少问题;(四)插图准备阶段的技术性问题;等等。插图一共104幅,都由傅雷亲自从各类书籍上选择,然后请友人拍成照片,再统一寄给出版社制版。这过程颇费周折,傅雷在1960年1月21日的信中对此作过详细的说明:
“《艺术哲学》插图用正式照片一套一百零四张,样片一套一百零四张,两者成本共计人民币一百二十一点一七元(另附清单一张)。摄影友人为此颇费心力;因图片取材方面不一,来源有十五种美术图书及零星照片,原来制版及印刷种类亦参差各异,为力求色调统一,便于制版计,多数须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一部分原底清晰度甚差,为尽量复制原来色调之对比、层次及细节,一种图片往往须反复用不同方法摄制、冲洗、试验至五六次方始满意者(清帐上提到废片,即指此种试验过程中所消耗之片),又有全部照片完成后,雷又在他处觅得更好之原底,交友重摄者。比较复杂的照片,并已请上海技术高级之制版厂看过,认为只要能用二套制版,用纸恰当,复制成绩绝对有把握。”
傅雷在翻译其他作品时,大概没有这样的麻烦,即使有插图,也不至于多达一百多幅。而且对这些插图还要进行编排、文字说明,这些都由傅雷一人承担。其工作细节,朱梅馥在1960年1月10日的家书中曾经述及:
“丹纳的《艺术哲学》年底才整理插图,整整忙了十天,找插图材料,计算尺寸大小,加插图说明等等,都是琐碎的而费手脚的,因为工作时间太长,每天搞到十一二点,做的时候提起精神不觉得怎么累,等到告一段落,精神松下来,人就支持不住,病了三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之于《艺术哲学》,已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译者,他同时又是一位编者。如果按照2000年3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那种编排,上册为文本,下册为图版,那么下册则可视为傅雷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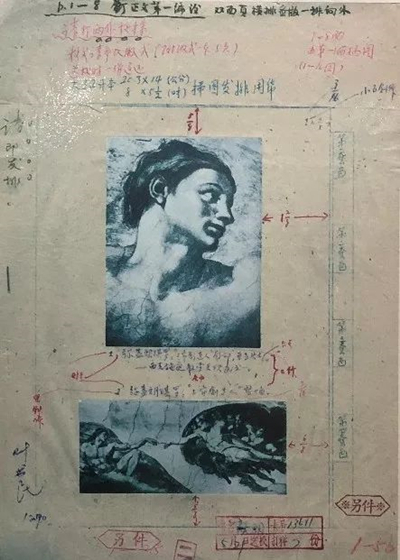
《艺术哲学》插图校样
上面只从校改和配图两个方面叙述傅雷在翻译、出版《艺术哲学》中所付出的劳动,另外还有一些琐事,比如纸张、版式、装订等问题,他也都一一核定。
对《艺术哲学》的偏爱和推崇 
虽然在“奉命之作”中“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艺术哲学》的缺点,但傅雷对该书的重视却屡屡溢于言表。他不仅在《译者序》中肯定了丹纳的实证主义,盛赞其丰富的史料,而且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手抄该书第四编《希腊的雕塑》,遥寄英伦,作为提高傅聪艺术修养的读本。其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一再提及此事,以证傅雷的爱子之心,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也说明了傅雷对《艺术哲学》的偏爱。
除了为傅聪手抄《希腊的雕塑》,傅雷对《艺术哲学》的推崇在家书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给傅聪的信中就说“丹纳论希腊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真是好极”。在一封给儿媳妇弥拉的信中,傅雷写道:“因你对一切艺术很感兴趣,可以一读丹纳之《艺术哲学》。这本书不仅对美学提出科学见解(美学理论很多,但此理论极为有益),并且是本艺术史通论,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以渊博精深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另一封致弥拉的信中他再次推介《艺术哲学》,盛赞它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读来使人兴趣盎然,获益良多,又有所启发”。这两段文字,可以视为傅雷对《艺术哲学》的总体评介。此外,他在和傅聪的通信中常常引用《艺术哲学》及丹纳的观点,并将其作为艺术批评的一种标准。比如谈到英国绘画时,他说:“英国画家水准之低实属不堪想象,无怪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第一流的英国绘画也批评得很凶。”不仅在美术上如此,在音乐中也是一样,不时地以丹纳的著作检验自己的观点:“读了丹纳的文章,我更相信过去的看法不错:韩德尔的音乐,尤其神剧,是音乐中最接近希腊精神的东西。”傅雷在“腰酸背痛,眼花流泪”的情况下抄录了《艺术哲学》第四编《希腊雕塑》寄给傅聪,显然并不仅仅因为它“好极”,还因为它“有用”。在给傅聪的家书中他提到了这种“功用”:“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
这些节录自家书的话语已足以说明傅雷对丹纳《艺术哲学》的推崇,而这一点往往不被论者所注意。在研究傅雷翻译的文章中,谈的大多是罗曼·罗兰的作品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固然是傅雷译著中的大宗,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哲学》在傅译作品中具有一种特殊性。为了揭示这一特殊性,我们必须从傅雷的翻译谈起。
一部“详尽的西洋美术史” 
一般认为,傅译的最大特色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不难看出,“神似”与“形似”都是中国画论的术语,傅雷正是借用美术的词语来诠释他的翻译观的,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的开篇写道: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临画与原画,素材相同(颜色,画布,或纸或绢),法则相同(色彩学,解剖学,透视学)。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
傅雷这种以美术解释翻译绝非孤例,比如他在和傅聪谈及自己修改译稿时也是以视觉性极强的词语来说明问题的:“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若非知道这是关于翻译的,还以为是在谈一幅画作。而且,傅雷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还借助图画理解情节:“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这里所谓的“工笔画”,是指巴尔扎克小说中对巴黎场景精细入微的描述,傅雷之所以能画出“草图”,也得益于他对巴黎及法国建筑的心得。傅雷的这些观念或方法绝不是“偶得”,而是他知识结构使然。很难想象,一个对绘画艺术一无所知的译者如何做到这样的融通。
《傅雷谈艺录(增订本)》,傅雷 著 傅敏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9
由此可知,虽然傅雷以翻译为职业并知名行世,但早期艺术史的训练不时地在他的工作中起作用。那么,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岂不是一桩美事?事实上,把翻译和艺术史结合起来——翻译艺术史著作——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理成章。傅雷另外两部艺术史译著显然就不是成功的范例。一本是译于1931年的《罗丹艺术论》。此书在傅雷翻译之前,已有曾觉之等人翻译过,因此有人劝傅雷不必“费事重译”,但傅雷宁愿“迻译为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前文述及,该书当时是上海美专的美学讲义,译毕后只油印过三十多册,在傅雷生前没有正式发表过。据罗新璋介绍,此书“译笔不乏高明之处,后来独树一帜的傅译某些特点已略见端倪”,优点是“文字不干枯,有华采,颇有文艺性”,但仍然有些弊病,包括“个别字眼显得老旧”,“行文不及后期傅译那样流畅,朗朗上口”等等。结合“迻译为自学一遍”及生前不曾出版看,傅雷对自己的《罗丹艺术论》译本并不满意,何况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还没有把翻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因此,此书便无法成为翻译和艺术史结合的完美例证。
另一本是《英国绘画》,译于1948年6月。此书在傅译作品里是一个“异数”。首先该书原著为英文,而傅雷译著大多从法文翻译过来,虽然他的英文不弱,但毕竟不是专长,难免流于平凡。其次,此书系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傅雷翻译的,而非他自己的选择。傅雷在选择翻译对象上要求极高,必须是好作品,还要符合他自己的文字风格,比如他虽然翻译过伏尔泰的作品,但因为风格不同,翻译起来特别累,终于没有作为主要对象。再次,傅雷对英国绘画颇有微词,虽然他对英国18世纪的肖像画和19世纪的风景画持褒扬态度。因此,《英国绘画》即使不是应酬之作,也绝不是傅雷理想中的艺术史译著,因此傅雷在与友人的通信及家书中鲜有提及。
《艺术哲学》与此前的两本艺术史译著完全不同。翻译一本自己喜欢的艺术史著作对于傅雷意义非凡,这便可视为他在翻译中付出比其他译著更多的精力的理由,也是他如此推崇《艺术哲学》的原因之一。
不过,《艺术哲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傅雷与出版社之间存在着分歧。傅雷在1959年4月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中,为要求在译著中加入插图,特地就该书的性质做一番解释:
“本书性质原系艺术史讲座,丹纳在一百年前巴黎美术学院所担任的讲座就是‘艺术史讲座’。丹纳在本书开头也有说明。所谓‘艺术哲学’乃是作者整理讲稿,预备出书时另起的题目;实际所谓‘艺术哲学’是作者解释艺术史时所用的观点与方法,一方面也是以艺术史来证明作者对于艺术的理论。……因此,人文出版此书,固作为文艺理论书籍,但实际上等于同时出版一部西洋美术史。我特别提出这一点,供诸位考虑问题时作参考。……而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比较详尽的西洋艺术史。”
可见,对出版社“作为文艺理论书籍”出版此书,傅雷虽不予以否定,但在他看来,它更是一部“详尽的西洋美术史”。而他在《译者序》中指出“《艺术哲学》同时就是一部艺术史”,显然也是出于出版社的定性极易引起读者的片面理解,才做这样画蛇添足式的强调。而《艺术哲学》出版以来,恰恰是在美学领域极受重视,而在艺术史界对其近乎集体沉默,这足以证明傅雷的强调并不多余。
《艺术哲学》,[法]丹纳 著 傅雷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1
翻译一部美术史对于傅雷的特殊性正在于把他早期的艺术史学习和教学与后来从事的翻译结合起来,实现了两种经历、两个学科的交汇。从这个层面上说——而非时间因素——《艺术哲学》是傅雷的一部总结性译作。但傅雷远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总结性译作,为中国艺术史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式,即以艺术史研究者的身份翻译西方经典艺术史著作以拓展国内读者的艺术史视野。虽然在傅雷之前已有不少学者翻译过一些艺术史著作,但大多为“艺术概论”一类的编译作品,而且重复颇多,而译者水平也参差不齐,大多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故大多数译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淹没在历史的记忆里。而傅译《艺术哲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影响数十年,除了傅雷名号的因素外,原著的经典及翻译的质量无疑是最大的原因。但这种经典著作加专家翻译的模式在傅雷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浙江美术学院史论群体所重视,从而翻译出一大批西方艺术史的经典作品,其中如范景中教授翻译的贡布里希的著作也已成为经典。在新的时代里,这种模式应该成为艺术史论界的共识,有更多的专家参与其中。这或许是傅译《艺术哲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地址:中国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 电话:8610-64001122
Copyright © 2013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权所有 | 技术支持:云章科技
ICP备 案 号:京ICP备12011204号-3